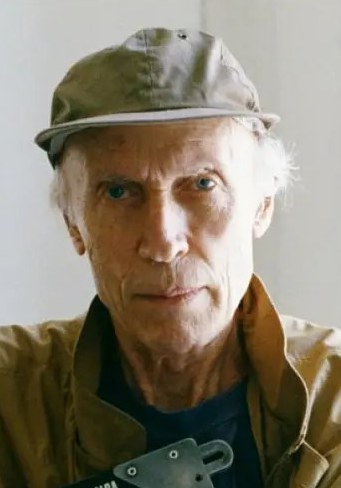人约巴黎 Les rendez-vous de Paris(1995)
简介:
- 三段发生在巴黎的爱情小故事,尽管启用的演员都很年轻,但看上去都有侯麦的味道。其一描述女孩怀疑男朋友欺骗她,于是打算在咖啡馆跟一名陌生人约会,岂料到达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其二描写一对男女在公园相遇,迅速相恋拥吻,并打算假装游客住进旅馆,其实女孩已有男朋友,一个意外发生 改变了两人的计划;其三描写一名小画家在咖啡馆约了一名瑞典来的游客,但偶然在博物馆门口遇上一名女子便一见钟情展开追求,不料她却是一名有夫之妇。
演员:
影评:
- ■文/小約
我們試著想像一九五五年,加西亞•馬爾克斯來到戰後的巴黎,觸目非創痍,恰是滿街滿座地打著吻,牆體刷著諸如“想像的力量”、“路面底下是沙灘”的漂亮標語。他寫道:“那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黑暗年代。街角上的樂師用手風琴演奏著思鄉的樂曲,街頭巷尾飄散著炒栗子的香味……在各種場合接吻的一對對戀人,火車上、地鐵裏、咖啡館和電梯中,戰後的第一代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愛情的公共消費,這是災難過後唯一廉價的娛樂。”
四十年後的巴黎大概還未有變,戰爭、爆炸、遊行,將時代的痕跡卷藏在簿冊史典裏,美國人還相信,只要電影拍在巴黎,皆關愛情。於是,侯麥拍出了《人約巴黎》,為不必與商業妥協便能贏得票房勝利立下典範。影評人跳起質疑:“侯麥又搞起了年輕人的電影,但是沒有比這個離真實走得更遠的了”。而事情證明,沒有誰比他更懂巴黎,沒有誰能比侯麥更知眩目時代年輕人的心。
同樣是三個故事,同樣是三個沒完成的戀愛儀式。侯孝賢是臺灣的,電影手工業下的記錄者;侯麥是法國的,電影工業之外的獨語人。一樣用著最為素樸的底色,描最精到的部位,一樣是不太照顧吃速食便當的速食主義者,一樣有大批食髓知味的小布爾喬亞迷族對之興味盎然。碗碗筷筷,洗洗晾晾,是侯孝賢;叨叨喋喋,走走轉轉,是侯麥。
小說家朱天文在《荒人手記》裏說:“按作者論,每個導演一生只在拍一部電影。那麼小津,他拍的就是嫁女兒。一個個體從所屬的團體脫離,加入另一個團體,為了世界的建立和延續。” 而侯麥的件件作品裏都插滿著浮世裏男男女女的情愛之憂、身不由己、口是心非、恍恍惚惚。侯麥的敍說是細婉、簡約、精巧,帶著旁觀者的冷冷的一副眼睛。朱天文說:“成瀨已喜男,比小津多了顏色,更無痕跡,更無情契的,紛紛開自落,比小津迷人。小津靜觀,思省。成瀨卻自身參予,偕運命一起流轉,他一生愛好是天然。”侯麥是近於小津的,他走步式、對談式的鏡頭如硬淨的容器,裏頭盛著感情。
“七點的約會”、“巴黎的長凳”和“1907母與子”是《人約巴黎》的三個故事,關於舊愛與新歡間充滿著自溺、軌外、割捨、背棄、飄渺不定的臨時而短暫的一瞬之夢。“七點的約會”裏的街遇、糾纏、丟失、偶拾、巧合,咖啡座裏世間男女的背信棄義。“巴黎的長凳”以文學之筆敍述一個有夫之婦每天都與作家情人暢遊巴黎的每一座公園。但她心裏只愛與情人坐在公園的長凳上,而拒絕情人寓所的沙發床。故事的末尾,她終於答應情人去一家心儀已久的旅館幽會,卻看到丈夫與另一個女人住了進去。她毅然與情人分手,因為情人與丈夫是“鏡子的兩面”,一面破碎了,另一面也無法存在。“1907母與子”短小而墨酣,濃縮了侯麥30年來堅持的浪漫哲學。名字源於畢卡索的一幅名畫,講述一個平庸卻又自負的小畫家,拋下陪他看畫展的女友,因為他對一個剛剛在展覽館裏碰到的女孩一見鍾情,並邀她參觀畫室。女孩說你已有女友,畫家說我與她毫不相干,女孩便與畫家討論他的作品《1907母與子》,並自己說幾小時之內就要離開巴黎,而畫家終是戀戀不捨。
如此像極學生作品般的情感小戲,三場約會邂逅,侯麥一一摭拾。本雅明很透徹得寫過:“大城市並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現,相反,卻是在那些穿過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緒中的人那裏被揭示。”侯麥的一管風景,獨獨落在本雅明的懷裏。
容我抄一截本雅明在描述巴黎拱廊計畫時說的話,沒見過誰能比他講得更好的了。“在每一部真正的藝術品中都有這樣一個空間,有一股涼風從中吹來,如同悄然降臨的黎明,吹向任何一個置身於這個空間的人。由此看來,歷史上被認為對於與進步的關係漠不關心的藝術卻可以標誌著進步的真正特徵。進步不在於時間流動的延續不斷,而在於對這種延續性的幹擾:即每當真正新生的事物用其黎明般的清新第一次降臨之時。”侯麥的藝術是古典而現代的,他在談到自己的電影很少用配樂時說自己在沈默的時候是最放鬆的,沈默不會使他有壓迫感。侯麥用默默無言語,任花自飄零的靜觀與悉心,處處散落著時代流動的痕跡。他的每一次創作,如新嬰垂跡。在同時代錯開一個轉身的空間裏,蕩開蓮底清漾的脈脈時間之溪。
《人約巴黎》極戲噱,極短促,如魚游水中,俶爾遠逝,如一夕西風,歡悰吹散,然我們所知道的是,自侯麥,而後巴黎,自巴黎,懷著愛。
原文地址:
巴黎的塔泰恩夫人咖啡馆,巴黎蒙特马的小旅馆,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它们是一幢被标记的建筑,是一个约会的地点,是一种邂逅的可能,但是当它们以随机的方式出现在男女的生活中,它们根本不代表巴黎,根本不趋向于确定的生活,相遇或偶然,相识或巧合,在匆匆的人群中成为一种湮没的风景。
“在巴黎相会,但不一定是在等你,也许是惊喜,也许不是明智的选择。”在巴黎的街头,男人拉着手风琴,女人穿着裙子,他们一起唱着,一种街头自娱自乐的表演构筑了侯麦“人约巴黎”的主题曲,男女之间的约会,应该是你等我或者我等你,应该是相互聊天坦诚相见,应该是更促进爱情的发展,但是约会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不明智的选择——当越过了理性,它就可能意味着巧合,意味着疯狂,意味着爱只是一个可笑的借口。
三个故事构成了“人约巴黎”的样本,“七点的约会”完全是一种巧合。埃丝特爱着男友霍勒斯,她遵守男友因为忙而提出“礼拜六再会”的约定,当好友菲利克斯告诉她晚上在格里斯家有个约会的时候,埃丝特也拒绝去参加,因为她不希望男友在忙工作的时候自己去聚会。这似乎是为爱做出的牺牲,正像女友赫敏告诉她,霍勒斯爱你胜过爱自己。所以埃丝特就是活在这样一种几乎完美的爱情里。但是那个秘密却一点一点被揭开来,菲利克斯说霍勒斯曾经在他们经常约会的塔泰恩夫人咖啡馆里和别的女孩在一起,赫敏也说曾经霍勒斯和两三个女孩交往过,起初埃丝特不相信,她坚信自己对霍勒斯的爱,也相信霍勒斯对自己的忠诚。
“我想做真实的自己,把感情隐藏起来太可怕了。”这是埃丝特的感情观,也正是有这种想法,所以对于别人的“风言风语”开始警惕起来,甚至陷入了某种不安。赫敏提出的建议是,你也去约会,让他嫉妒。喜欢真实的埃丝特本应该拒绝这样的建议,但是内心的不安又让她犹豫,在一次市场买菜的过程中,有个男人上来搭讪,后来想要埃丝特的电话,埃丝特也是拒绝,但是最后她在离开之后却转身回来,告诉他如果可能就在塔泰恩夫人咖啡馆见面。
这是埃丝特自我怀疑的开始,也是对霍勒斯所谓忠心质疑的第一步,当她发现自己在买菜时钱包丢了,之后又有一个叫阿里西的女孩捡到了钱包,交换给她的时候,她想到了在市场上缠着她的那个男孩,于是心里怀疑是他偷了自己的钱包,但是在她转身回去的那一刻开始,她对他的好奇心已经占据了上风,她甚至告诉阿里西知道谁偷了钱包,“他还很帅的。”在这一刻,对于小偷的定义已经被改变了,他是一个很帅的男人,是一个令人好奇的男人,或者也是可以对霍勒斯实施报复的对象。
终于,阿里西说自己要去塔泰恩夫人咖啡馆,和刚认识的男孩约会,起初只是问路,埃丝特说自己也想去,因为和那个在市场碰见的人也有过某种约定,她更想知道是不是他偷了钱包。两个女生去了咖啡馆,不想那个正在等着阿里西的男孩就是霍勒斯,那一刻是尴尬的,至少对于霍勒斯来说,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样一种偶遇,一边是自己的女友,一边是刚刚邂逅的女孩,他们一起出现。而这也彻底揭开了埃丝特困惑的感情,所以她装作是阿里西的朋友,和霍勒斯打招呼,满面笑容地看着这场谎言被揭穿的好戏。
其实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了,埃丝特以有事为理由离开了咖啡店,霍勒斯追上来,告诉她和阿里西没什么,而且也甩下她来向你解释,但是任何解释对于埃丝特来说都是无意义,所以她快步走开,仿佛要告别这个充满巧合的约会,也告别这一段看起来必然的爱情。偶遇和巧合,注解了邂逅的意义,或者霍勒斯的确和阿里西是邂逅之后的相识,也构不成谁爱上谁的问题,而埃丝特对于那个市场里的帅男孩也是邂逅,即使她有着某种报复的心态,也只是一种游戏般的存在,但是当这些充满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其实最终走向了必然:必然的背叛,必然的结束——就像那个在市场里出现过的男孩,是不是他偷钱包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甚至在空着的位置上坐下来,可能在等埃丝特,可能在等别的人,总之,他作为一种偶然的存在,和埃丝特发现秘密之后的故事完全无关。
巴黎约会场景中的小小奇遇记,却导向了一种必然,这不是惊喜,却也是惊喜,而巴黎似乎也成为一种想象的符号,起初埃丝特和阿里西在一起的时候,埃丝特说自己就出生在巴黎,“这就是巴黎。”像是对巴黎充满了无限期待,就像对自己和霍勒斯之间的爱情,但是当这一幕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巴黎让我恶心。”就彻底解构了她对于爱情的向往。是爱情被揭穿,巴黎也被揭穿。而在《巴黎的长凳》里,所谓的爱似乎也是一种邂逅,它走向的是一个更为奇特的结果。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他们的约会的地点从公园到公墓,似乎他们在一起总是充满了期待,但是每一次的话题里都出现一个叫贝努瓦的男人,他是女人的前任男友,说是前任,却还有剪不断的关系,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同居状态,也没有宣布走向了分手,女孩只是希望能顺其自然,能在事情发展成熟后走向终结,但那时她又和另一个男人交往,甚至说:“我爱过他,甚至比爱你更深。”这当然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而且当每次话题里都出现贝努瓦,实际上是女孩根本没有做好彻底忘记的准备:在美迪奇喷泉公园里,她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为的是不让贝努瓦看见,“他会使我感到羞愧。”在圣文森特公墓,她说起和贝努瓦刚认识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要拉过她的手,但是她却喜欢这种感觉;在蒙苏里公园,她说贝努瓦从来不像你一样懂得各种知识,他好像对什么也没有兴趣。
男人和她在公园里约会,他们的话题谈及的是另一个男孩,而且男人几次试图邀请她去自己住的地方,女孩也总是以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为由拒绝,后来她想出了一个出行计划,那就是“巴黎一日游”:两个人扮游客,像是第一次来到巴黎,完全将自己变成巴黎之外的人。这似乎在寻找一种浪漫,或者制造一种刺激,终于他们拿着行李,从车站下车,拿着地图坐地铁打听蒙特马的那间旅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是快乐的,也是疯狂的,没人知道他们本来就是巴黎人。
让自己成为非巴黎人,以进入巴黎的方式寻找存在感,这是不是自欺欺人?而当他们终于像演戏一样找到那间没有神秘感的旅馆,突然发现贝努瓦也带着另一个女孩走进了旅馆,看见了他们的女孩终于感觉自己被爱情抛弃了,当男孩欣喜地说:“这下我们自由了!”女孩却顾自走了,她对紧随着的男孩说:“你只想着自己,却不知我的感受。我们到此为止吧。”本来男孩以为这是他们感情进展的最关键机会,一种感情结束就意味着新一段感情会没有顾虑地开始,但是女孩却宣告他们也结束了,她的理由是:“从一开始,你和贝努瓦之间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你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你是他的影子。”
说起的话题里都是贝努瓦,总是拿贝努瓦和他相比,这是一种顺其自然?更是一种自欺欺人,男孩的确是贝努瓦的影子,而当本体消失,影子也没有了意义。而这也是巴黎的命运,两个都生活在巴黎的人,想要用“巴黎一日游”来完成一次出行,是一种人为的隔离,是想要一种刻意的陌生,实际上这个幻想中的巴黎也依然是影子,影子是必须依赖本体而存在的,巴黎是另一个消失的本体,和贝努瓦一样,成为这个游戏最关键的一部分,最后只留下那个不想成为影子的男人,在巴黎的街道上成为最孤独的风景。
邂逅了不爱自己的男人,才是真正新的开始,无论是《相约七点》还是《巴黎的长凳》,都是一种影子的消失作为结果,而在《母与子1907》中,影子似乎开启了另一种可能。画家被朋友介绍认识了来自瑞典的女孩,但似乎他不喜欢她,他们在画家的工作室聊天的时候,的确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女孩说她的画作阴郁,那些人很困乏地走在路上,另一幅画里的人像是在集中营,而他说,画作中的褐色象征着生命的颜色;当他们走出工作室,女孩说巴黎的这条街到处是灰色,一点没有感觉,她喜欢亮色;而画家说他喜欢破旧的东西,“如果巴黎变干净了,我不会描绘它。”两个人眼中的巴黎,两个人心中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男孩和女孩当然在巴黎是不会相爱的。
但是,在男孩送女孩却往毕加索博物馆之后出来,却和一个红色衣服的女孩擦肩而过,于是像有了某种触动,他转身跟随着女孩,女孩进入的正是他不喜欢的毕加索博物馆,终于他有遇见了那个瑞典女孩,但是这次他故意和瑞典女孩聊毕加索的画,以此来引起红衣女孩的注意,当红衣女孩离开,他又跟随她,终于在街上告诉她她是自己感兴趣的女孩,而女孩告诉他,自己在等丈夫,他们刚刚结婚,在蜜月期。但显然,女孩对画家也有着某些兴趣,她来到了画家的工作室,没有对那些画作表示不喜欢,甚至还问他是否愿意为自己画画,他们谈到了毕加索《母与子1907》,谈到了博物馆里的瑞典女孩,“忽视不感兴趣的人是为了接近感兴趣的人。”画家这样说,他不自我谴责对瑞典女孩的冷漠,而是极力想证明面前的她才是自己喜欢的女孩,而女孩却要走了,她最后拒绝了画家亲吻的想法,“你厌倦平庸的人!这一点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最后女孩离他而去,在楼梯上她说,去找那个瑞典女孩吧。
也是一次邂逅,但是和前两段故事不同,画家对女孩,女孩对画家,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兴趣,只是女孩已经有了丈夫,她更在道德意义上坚守了自己的原则,而画家也是在理智中没有做出更出格的动作,当女孩最后说他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仿佛是一种触动,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画作,终于在那一些疲乏地走在路上的人群里,出现了一个穿着粉红裙子的女人,在灰暗色的色调中显得格外显眼,而这一笔明亮的色彩,似乎又是画家对巴黎的另一种改写,当初他对瑞典女孩说自己喜欢的是灰暗,是沉郁,是破旧,这是一个在红衣女孩出现之前的巴黎,而现在,当那个感兴趣的人出现又消失,在他心里来说,却是一次超越平庸的开始,巴黎是个机会,巴黎更是最后的生活,只有不断地改写才能发现新的美好。
男人和女人,约会在咖啡馆、公园、旅馆,巴黎的生活是多变的,是充满了可能的,当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咖啡馆都会有故事发生,这是巴黎的偶然性:如果埃丝特不遇见阿里西,她或者还深信霍勒斯对自己的爱,或者也会去尝试一次邂逅,而之后的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去蒙特马旅馆的男孩和女孩如果没有看见贝努瓦,他们也许就在“巴黎一日游”中上演了“巴黎一夜情”,以及后来的真正在一起都是并不意外的事;画家如果没有遇到红衣女孩,或者在路上还会遇见一个紫衣女孩,而且紫衣女孩没有结婚,他们聊得十分投机,甚至最后他们真的成为了情侣……有太多的偶然发生,有太多的邂逅存在,巴黎是机会主义者的天堂,“不期而遇才是最好的邂逅。”就像后面两个故事的男人和女人,连名字都没有,他们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是这一种巴黎是虚幻的,是想象的,是影子般的存在,甚至仅仅是一个符号,而真正的巴黎在侯麦镜头下,一定是一种必然:必然被揭穿的谎言,必然是走进旅馆的贝努瓦,必然出现在画作上的光线和色彩。
从偶然的邂逅开始,到必然的离开结束,巴黎还是那个巴黎,因为每一种期望进入邂逅状态的人还在,巴黎却已不再是那个巴黎,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影子被去除之后看见了真实的自己。
第二段故事展现了三角关系中最为微妙的一面,在Elle的不知名丈夫和她的情人Lui之间有一种相互推拉、互为补充的镜像关系,一个做事带有很强目的性,另一个随时随地享受惊喜,一个向往郊区,一个住在城里。
这其实有点像立体主义绘画,正如第三个故事中画家对毕加索的评价:“他总是想呈现出所有的视角。”《Girl before a Mirror》呈现的是年轻与衰老,《Large Nude at armchair red》则是身体的内与外。
 Large Nude at armchair red
Large Nude at armchair redLui曾义正言辞地纠正“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画家而不是超现实主义”,但有意思的是毕加索最毕加索的地方就是他从不拘泥于某一种风格,他总是在熟悉了一种风格之后又飞快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尽管侯麦只展示了婚外情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轻易地想像出Elle和她丈夫的相处模式,这种想像甚至具体到可以被特定的居室空间外化。侯麦对居室的强烈关心几乎体现在他的所有电影中,他会细致地安排每一处生活痕迹,力求体现出居室主人的艺术品位与生活习惯。这种关注总会让我联想起现代侦探小说,正因为居室成为了一种与工作场所、大众娱乐空间完全相分离的私人空间,才诞生了那些通过私人物品、家具布置上遗留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的神秘职业。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居室空间中遗留的痕迹其实相当于蝉翼蛇蜕,似是而非,因此身份的匿名性、自我认知的摇摆也可以放在这一题材中讨论,比如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
Elle和Lui这段婚外情的发展与对熟悉城市的陌生区域的探索相互交织,这一点在假装游客的游戏中体现地最为明显。Elle要的是探索未知的兴奋,或者说是换一种视角(城郊的视角、俯瞰的视角)重新定位日常的冲动,而不是在日常之中体验非日常。从这个意义上说,Elle和Lui漫游巴黎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具有现代艺术精神的尝试。


在Elle决定和丈夫分手之后,她与Lui在一个温室花园中碰面。这一段中很多镜头都让我想起马奈那幅《The conservatory》,甚至这一段故事的标题《巴黎的长椅》都直接出现在了画中。对比马奈的绘画,可以看出在侯麦这里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似乎对调了,Lui成了那个仿佛失去知觉的木偶,Elle则以其诱惑性的动作操纵着她的情人。
 The conservatory
The conservatory

在马奈的年代,温室这样一种隐蔽而封闭的环境就像是专门为婚外情而生的一样,这样一种环境在保留着一部分原始面貌的同时又与真正的自然相去甚远,它们是文明荒漠中的人工绿洲,它们的存在就建立在与城市之间的辩证对立关系之上,从而标志出都市生活的缺失、机巧与伪饰。
- 看过不少导演拍摄的巴黎,但就属侯麦的这部最特别,在侯麦的镜头下,巴黎不再仅仅是一个“浪漫之都”而已,(美好的让人感觉它仿佛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于地球上的城市)。
侯麦的“巴黎”,更像是巴黎人拍摄的巴黎,让人感觉很亲切,亲切到仿佛作为观众的自己就是巴黎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电影剧情本身,本片为三段式故事,继续着侯麦说了一辈子的有关于男人与女人,爱情与欲望的故事。
第一段:是一个”多角恋”故事,被演绎为一部类似于微型悬念小说的结构,一个女孩怀疑自己的男朋友早已另有新欢,于是就决定找一个”新男朋友”来刺激一下对方,没料想,这位“新男朋友”居然是个偷她钱包的小偷(侯麦很喜欢以金钱来考验自己电影中的角色们)。但钱包却意外的被一位好心的女孩见到,但更让她没有料到的是,这位女孩子竟然是她(原来)男朋友的新女朋友。是的,听起来一个极其复杂故事,
但总的来说,可以把这段故事称之为是”妙趣横生”。
第二段:一个男人几乎用尽了吃奶的力气说服一个女人离开自己原来的男友,与自己双宿双飞,待他即将要成功之际,女人才发现自己的“前任男友”早已先她一步,与人“红杏出墙”了,她顿时失去了对眼前这个男人的兴(性)趣,也使作为观众的我大失所望。(笑)
这是侯麦又一次把观众玩耍于鼓掌之中的成功尝试。
第三个故事:描述了一个事业并不得意的画家一次失败的“勾女”经历,(还属于“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段故事本身并不比以上两个故事有趣,但在此期间,侯麦却“慷慨”的让我们欣赏了大量的毕加索的画作,并假借画家之口陈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
对有意研究侯麦的人士来说,此段实在是有很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