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Verdens verste menneske(2021)

又名: 世上最烂的人(港) / 世界上最烂的人(台) / 尤利娅生命的十二段律动 / 世界上最坏的人 / Julie (en 12 chapitres) / 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
导演: 约阿希姆·提尔
主演: 雷娜特·赖因斯夫 安德斯·丹尼尔森·李 赫伯特·诺德鲁姆 汉斯·奥拉夫·布雷内 Helene Bjørneby 威达·桑登 玛丽亚·嘉西亚·狄·梅奥 Lasse Gretland Karen Røise Kielland Marianne Krogh 西娅·斯塔贝尔 Deniz Kaya Eia Skjønsberg 鲁比·达格纳尔 Torgny Amdam Rebekka Jynge Sigrid Sollund Are Skeie Hermansen Siri Forberg Sofia Schandy Bloch
上映日期: 2021-07-08(戛纳电影节) 2021-10-13(法国) 2021-10-15(挪威)
片长: 128分钟 IMDb: tt10370710 豆瓣评分:7.9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故事聚焦当下的奥斯陆,围绕年轻睿智的女性朱莉展开。30岁的她仍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尽管她与事业有成的制图员阿克塞尔彼此相爱,拥有强烈的安全感,并很开心和他在一起,但她拒绝给渴望孩子的阿克塞尔生子。朱莉决意离开阿克塞尔前往艾文德,希望能够开始新的生活……
演员:
影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生育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热点。光是为人母的社会-自我期待与鬼门关走一遭的风险间的残酷冲突,国内(《生门》、《人间世》这样的纪录片)国外(如《女人的碎片》)的影视作品均有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在社会福利和平权建设方面一向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在这一题材近年来更佳作频出,如丹麦电影《爱在你手心》、《第二次机会》和瑞典电影《宾馆》(“机械姬”艾丽西亚·维坎德饰演一位因提前分娩未能按预期时间剖腹产而抑郁的新手母亲)。
而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将生育问题温柔地融合到“生”、“死”、“爱”的永恒讨论之中。作为一部绝对的女性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不仅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还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有力竞争者。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角朱莉(Julie)是一位典型的北欧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福利都唾手可得的背景下,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事业、伴侣和人生轨迹。自由是她的首要价值,而这份自由却又带来些许迷茫。随性的她最初学习医学,却因为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远多于对人类躯体的兴趣而半途而废。兜兜转转到30岁时,她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业余爱好是摄影。她也尝试写作。她的男友阿克塞尔(Aksel)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已经40多岁的他期待着一个孩子。而这成为了两人矛盾的焦点——
阿克塞尔说不清为何想要孩子,大概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有孩子,而年长朱莉十几岁的他的人生也趋于稳定。而朱莉恰恰相反。朱莉说不清为何不想要孩子,大概是直觉孩子将会阻碍她的自由。朱莉也隐隐感到自己无法自得地融进阿克塞尔的家庭和事业。在阿克塞尔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她若无其事地离开,溜进一个婚礼party拿酒喝,假装自己是医生跟年长的阿姨们说母乳哺育会养出精神病的孩子……
也在这个party上,朱莉和素昧平生的男二号艾文德(Eivind)玩了一场假装出轨的游戏:一对分别有爱人的男女在亲密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饮同一杯酒,互相讲出隐藏最深的秘密,互相观察对方小便……并嬉笑着判断“这算/不算出轨”。
艾文德关心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人类的存在感到羞耻(这样的关怀和羞耻感在当今北欧年轻人中极为普遍),因而也不想要孩子。终于某天,朱莉离开了阿克塞尔,奔向了艾文德。但新的隔阂也在浮现……
对中国观众而言,北欧女性朱莉提供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投射,又提出了我们未来或许将面临的问题。如果说东亚女性在层层期(束)待(缚)中的状态是消极、倦怠而无从逃离的话,那么已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里,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在对抗性关系隐去后,如何在“我孑然一身存在于世间”这一处境中锚定自己,进而发展出方向、道路和力量。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这个动力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当一位女性不再受到来自宗教或礼教传统的显性束缚,也不受到与权力关系相伴的隐性束缚,当她在身体、性、亲密关系和婚姻上都具有绝对自主时,她为何仍怅然若失,时时需要从一个人身边逃到另一个人身边?
这种飘零的、无依无靠的感觉,正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世界的写照: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轻易结束。曾经人们以为神圣和庄严的纽带,现在都瓦解了。失去了这些坐标的女性,该如何定义她自己呢?正像影片中最精彩的迷幻蘑菇一节,朱莉感到脚下的土地慢慢坍塌下陷,她终于无立足之地而飘荡。在幻觉中,朱莉看到了自己垂垂老矣的样子:经过哺乳的乳房严重下垂,四肢骨节突出,小腹和臀部的皱纹一层层耷拉成一片片臃肿。
清醒后,恐惧的朱莉披着被子在艾文德的怀抱里寻求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当然也是暂时的——朱莉随后就会发现艾文德完全不像阿克塞尔那般能欣赏她的作品。但显然阿克塞尔也不是一处可以永久停驻的港湾,因为向往自由的朱莉根本不愿停驻于任何一处港湾。
如果不是女主角(现在是戛纳影后了)的表演以一种惊人的天真和坦诚(如她笑着承认自己需要确认自己的性吸引力)感染了观众,这样一个角色恐怕很容易被骂“矫情”和“作”。尽管如此,豆瓣评论区亦有不少人批评其为虚弱的“田园女权”,批评其恃靓行凶,心智停留在儿童水平云云,甚至连女主最终成为摄影师也解读为给画家前男友拍照而“依附”了男权的力量。
这样的争鸣比电影本身还要有趣。因为它反映出的与其说是某种原教旨的文化差异,不如说是与性别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差异:在这个地球上,当一些女性在争取被动的自由时,一些女性已在探索主动的自由。后者可能因为对我们过于陌生而显得荒谬。而这样的探索哪怕看起来矫情、虚弱,如无头苍蝇般无处着力,也依然是珍贵而有其启迪意义的。
何况这样的探索明明是有现实根基的。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远方早已不是远方,他人的生活同样能在本土激发新的震荡。正如笔者本人的遭遇:
笔者在丹麦居住时的房东是哥本哈根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在那年的圣诞节他告诉笔者,年轻时他曾订婚,却终于因为恐惧失去自由而逃婚。彼时彼刻,他的朋友们都和家人庆祝圣诞,他只能和年迈的母亲形影相吊。他由是叹息自己必须为年轻时的选择承担今日的孤独。他又告诉笔者,他的部门有多位专注事业的女下属在步入四十岁后,突然由不婚不育主义开始疯狂想要结婚生子。但结婚生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听到这两件事的那一刻,笔者确实震惊了——在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女性面临的生育选择竟然有这样一个向度。这是二十多岁的笔者不可能想到的。
在那里,生育问题或许不再受经济因素和权力关系的宰制,但生育问题仍和对衰老、死亡、孤独相连,和时间的不可逆转相连——在我们那单行线的生命面前,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而那些自相矛盾、左右横跳、甚至自己打脸的尴尬窘迫,也正是生命的真实样子。
于是,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在《奥斯陆,8月31日》和《盲视》后,成功地挖掘出生育问题背后的死亡焦虑。而死亡焦虑也是他作品序列的一贯主题——时光流逝,墨水会流干,画纸会烂,人的肌体会形销骨立(如阿克塞尔患癌症后的样子),艺术家的创造力会干涸。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承载着某种朝向永恒性的寄托(如中国古人所说的“立言”),而这样朝向永恒地凝视反而确证了生命的有限——永恒的不可能性。
于是艺术的尽头也都是不得其解,杳杳指向只能嘶吼着我要活着那一天,正如影片结尾处,阿克塞尔坐在车上向朱莉痛苦诉说,我真的不想流露出脆弱,但我真的痛得无能为力;我不想在作品中被人铭记,不想作为记忆被你铭记,我想活着,我想和你一起生活,happy after。
而朱莉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死生亦大矣。在死亡面前,生的力量就算不是不存在,也是微乎其微。朱莉拼命从阿克塞尔那儿寻求确认(“你将是一个好妈妈”),似乎期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来挥散死亡的阴影,却在阿克塞尔去世后流产。——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那种“死亡之后亦有新生”的流行叙事,被本片无情打断。(而可资对比的一个有趣例子是,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浓墨重彩刻画或轻描淡写带过的死亡远远多于新生,甚至没有新生。)
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逝去也宣告了朱莉和艾文德“新的篇章”的完结。如果多数婚姻是在孩子的润滑作用下维系的话,那么一个人晃晃悠悠也未尝不好?在影片的结尾,成为摄影师的朱莉发现前男友一个去了天堂,一个已和别的女人生育孩子。但她还是那副天真可爱的神态。
影片终结于朱莉的孑然一身。而孑然一身却未必是孤独。它也许是自给自足。谁说女性的自给自足不是一种美丽的状态呢?
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短名单终于在近期公布,横扫欧美各大颁奖台的《驾驶我的车》,普遍被外界视为今年最有可能摘得此项殊荣。
不过除它以外,另一部戛纳系的作品也非常有意思,它就是来自挪威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奥斯陆,8月31日》)对观众而言也许比较陌生,但他的电影却在圈内小有名气。
今年的这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讲的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讲的是当代年轻人普遍面临的问题。
女主Julie,一个原本在医学院攻读学位的高材生,因不满整天做手术带来的枯燥乏味,决定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为此,她更换了专业,攻读起感兴趣的心理学。


可过了没多长时间,她发现自己对心理学也丧失了兴趣。比起对内心的探究,自己果然只是个视觉动物,于是,Julie再次退出,选择用学生贷款购买了专业设备,打算今后以拍照谋生。
专业变了一次又一次,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aksel的出现让她暂时拥有了一段还算稳定的关系。不过很快,Julie又觉得不对劲了。
比起事业有成的Aksel,只是一个学生、靠在书店打工拿着微薄薪资的她什么都没有。看着男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鲜花掌声和书迷的崇拜,Julie很郁闷。

不堪忍受如此落差的Julie借故早早离开,返家途中,她看到了一个正在举办新婚庆典的party,打算潜入其中排解此前的低落情绪。
派对上,Julie结识了另一个男子Eivind。
虽然只是一次偶然邂逅,但两个人都发现彼此相当来电,甚至已经有了擦枪走火的前兆。
影片采用章回体叙述,来到两人邂逅的这一章,标题起名“出轨”,但这种出轨并不来自肉体层面。尽管两人管住了下半身,颇具暧昧的互动,却将他们的真实想法传递给了对方。

果然,这次经历并没有让Julie忘掉Eivind,以至于影片必须要用一个时间凝固的超现实段落,来表现Julie”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骚动心理。
至此,“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指代的是谁已经了无悬念,没错,那个人就是喜欢反复无常的Julie。
导演毫不留情地将矛头指向Julie,并用生动和极富真实感的生活琐碎,为观众还原了那些一直打着“自由”旗号,却始终无法让生活走向正轨的一类人。
讽刺的是,不光他这么讲,Julie自己也深有体会。

或许这样的批评有些不留情面,甚至有些冒犯,但就像刚才所讲,它的确反映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的问题——
脑子想的永远比实际做的丰富。
可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深耕,并等待自己的付出开花结果?Julie大部分时间是不知道的,她总是习惯用“不知道”来回答男友提出的现实问题。
Julie和Aksel巨大的年龄差难免会被人抨击为不切实际,但在这个“爱最大”已成为共识的年代,年纪已经无法成为判断情侣关系的标准,更何况,他们的磨合可比大多数人来得幸运,除了没小孩,这段关系大部分时间是完美的。

导致Julie不停尝鲜的原因,影片提供了一个切口供观众解读。
单亲家庭成长过来的julie和生父一直见少离多。难得的生日聚会,对方也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参加。
Julie看到了父亲再婚家庭的现状,知道他在撒谎但并未戳穿,从小到大的父爱缺失,一定程度上的确给了她不安全感,为此,她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来获得稳定。

所以当Aksel询问她是否要造人时,Julie才会愤怒地拒绝,她不希望依靠他人意志存活,这样没有存在感。但将锅甩给男方的强势和操纵,其实也只是她用来逃避现实的借口。
事实上,对于人生接下来该怎么走,Julie基本是一团浆糊。
这并不是她的错,因为她的阅历注定了她必须经历更多才能看清未来,所以影片中,她才会不停更换跑道,继而陷入下一轮迷茫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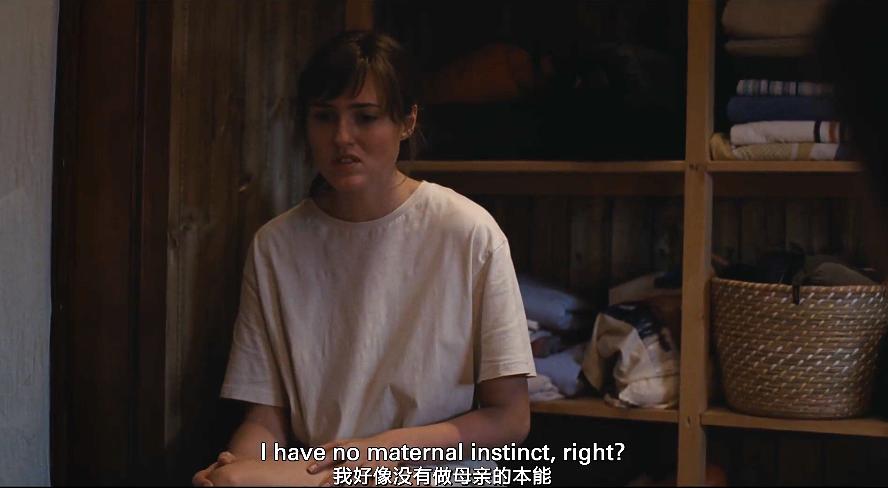
相比之下,男友Aksel就理性很多。
他知道和Julie之间的关系需要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既然选择了,也会果断向前,一步步规划属于两人的未来——尽管这对喜欢变化的Julie而言有点亦步亦趋,甚至呆板。
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根源来自于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和Julie分手后,Aksel因绝症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探病期间,两人展开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Aksel告诉Julie,自己所处的年代网络不够发达,那是一个需要靠双手去发掘周边事物的年代,以唱片和书籍为例,所有的文化符号都是具体和可被亲手感知的。

新生代则不同了,一出生就被信息覆盖的他们面临着诸多选择,一切都能通过快捷方式得到满足,但认真体验一件事物的乐趣,亦随着海量信息的冲刷荡然无存。
Julie身上的缺点就是这个时代负面的集中体现,经由数字信息喂养起来的他们看似什么都懂一点,但能系统了解事物全貌的人已经不多。过于分散的精力让他们很难专注于同一件事,同一个人。
什么都很有趣,但很快又会随着下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变得索然无味。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代青年看似活得潇洒自由,但未必比老一代人更通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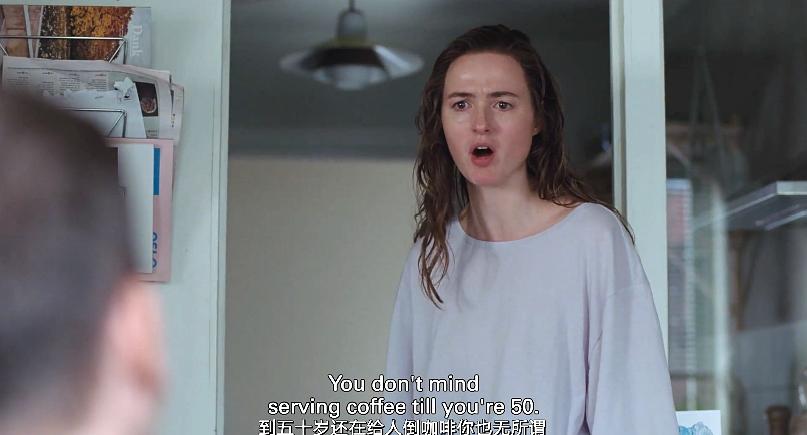

看看Julie随后和Eivind不断恶化的关系,再看看她所处的舆论环境,一切都在表明:我们的生活并不因为便利变得多元,反而因为过分便利而拉低了人类智思,变得越发激进和趋同。
新鲜劲头一过,Julie很快意识到新任男友不过是一个咖啡厅的杂工,而她要的不止新鲜那么简单,所以她只能又一次提出分手,不管对方是不是对的人——就和当初的Aksel如出一辙。
网络大数据带来的阵营分化,让人已经无法再心平气和地看待不同观点,有的只是非黑即白的标签化和恶毒的攻击。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准前进方向,何止Julie,身处其间的你我皆会迷茫。
好在人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动物,我们能从不断的错误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路。糟糕的不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糟糕的是我们看清了问题本质,却仍旧无动于衷。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提尔导演“奥斯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我是从第二部《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开始看的,因为很喜欢又去看了前作《重奏》并盼星星盼月亮整整一年盼来了这部终章。昨天看完电影后又去看了导演的一段访谈,导演说自己花了很长时间走过奥斯陆的街道,观察这座城市。许多人会问,那么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变化?你又在做什么分析?提尔导演说作为电影导演,他只是负责呈现,观众可以自己感受这座城市十多年间发生了何种变化。

在看《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时我就十分倾心于电影对奥斯陆城市景色的描绘,开头的许多模糊的自述既有对奥斯陆的城市记忆,又有仿佛是熟悉的人对男主的回忆。





 最后是菲利普大厦的轰然倒塌。
最后是菲利普大厦的轰然倒塌。
导演在访谈中也特别提及了《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开篇的这个镜头,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镜头。Anders从静谧的乡村Rehab回归城市,穿过黑暗的隧道眼前突然一片开阔,是一个在建设中的城市,耳畔响起a-ha的《I've been losing you》。可以想象Anders在Rehab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他离开的日子里不仅是亲友发生了变化,这座城市也在改变它的模样。

而这片正在施工的建筑群就是Eivind提及的奥斯陆条形码计划。我也是在他提及这个词儿之后才了解到这片建筑的故事。 根据网上的资料,奥斯陆条形码计划是2003年开始的,峡湾城重建项目Bjørvika的一部分,因为其建筑群的形状被称为“条形码”。

项目最初的目标是在保证城市空间的灵活性、建筑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在奥斯陆市中心滨水区,塑造一个有良好步行环境的片区。项目地块是处于火车轨道和峡湾之间的狭长区域,总体规划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筑建造控制原则,包括重要建筑物的高度、宽度控制、建筑物之间的最小间距等,以避免在滨水区域形成一堵大墙,阻碍北侧城区与水岸的联系,并且缓解城市发展压力,不减少现有的绿地空间。建筑体量控制方面,首先是将片区划分成较窄的条形地块,由于形状相似,被称作“条形码”。另外,提出建筑物之间至少要留出12m间距的控制要求。 作者:Visible_City 出处:bilibili
 Eivind与Julie不对等的秘密交换
Eivind与Julie不对等的秘密交换
电影中的时间静止片段,我想主要是服务于提尔导演展示奥斯陆街道的愿望。因此Eivind被安排在条形码大楼里端咖啡,而Julie跑过大半个城市去找他。一路上的风景就是奥斯陆十五年的变迁。
 条形码建筑群的近景
条形码建筑群的近景历经10余年,条形码区域基本建成完成,这是一次重塑城市景观的绝佳尝试,在保证充足公共空间的前提下进行城市功能和空间的更新,并且赢得了多个国际奖项。但是,这个项目也是奥斯陆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不同的社会群体,包括专业人士和市民,都对建筑群的高度和设计提出过广泛批评。反对的人们认为,这个建筑群成为了峡湾与其他城市空间的屏障,破坏了奥斯陆原本低密度开放的城市景观特征。2007年,反对建造高层建筑人士组织的情愿活动中,收到超过3000个签名。根据同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奥斯陆71%的人口反对该项目。另外,许多专业人士认为,这个项目的设计“几乎没有关于奥斯陆的文化和历史痕迹”。项目建筑师声称的“为特定环境做出相应设计”在项目中很难体现,也并无迹象表明建筑师实际上在他们的工作中融合当地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特质,最终的设计中也没有能够反映社会环境的建筑,条形码街区只是一个特定人群使用的商业办公区。尽管遭到众多非议,项目建成后不仅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商业办公片区,也变成了众多旅游者的目的地。在2016年威尼斯双年展,完整的条形码项目和其中五栋建筑被展出,知名度大幅提升。从那以后,条形码项目已从一个争议不断的城市片区变成了奥斯陆的象征。 作者:Visible_City 出处:bilibili
我很喜欢提尔导演在作品中融入的理念,场所与记忆的关系。那些生活过的地方本身就带着无法复现的记忆。

本片结尾Askel带Julie去看自己儿时居住的公寓,那几块红黄蓝的彩色玻璃镜头勾起了我无比伤感的心情。我能想象出童年的Askel透过这几块玻璃观察着窗外的世界,又在成年后把这些色彩画进自己的作品。我能想起自己童年时也曾看过的某块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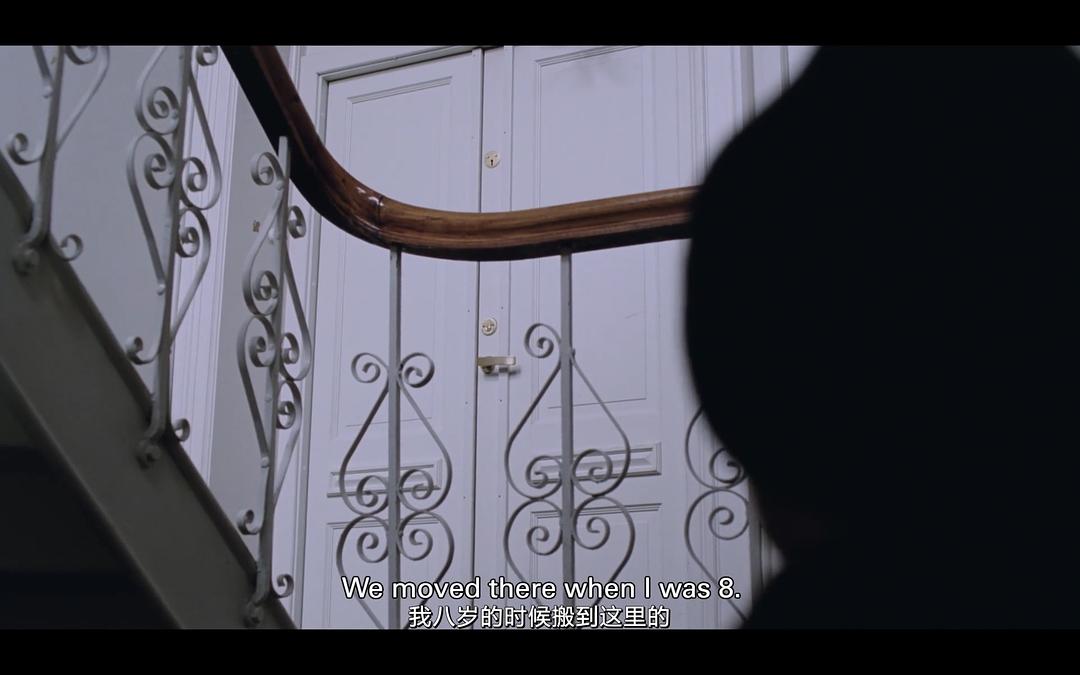

 Askel说这些颜色是他画漫画时的重要参考
Askel说这些颜色是他画漫画时的重要参考 Askel家里的挂画,正是红黄蓝玻璃的颜色。
Askel家里的挂画,正是红黄蓝玻璃的颜色。 今天发现开篇就是四色玻璃的颜色
今天发现开篇就是四色玻璃的颜色导演也有提到两位记录纽约的导演,Spike Lee和Martin Scorsese,我以后也会专门找来他们的作品看看。我喜欢看那些主角无所事事行走于城市街头的电影,让镜头把鲜活的彼时彼地捕捉下来。也许只需要十年,那些曾被记录过的地方就会消逝,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回忆又该如何寄托? 提尔导演做了我一直想做的事,从2006年的《重奏》到2021年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Anders从新出道的年轻作家变成了四十多岁沧桑的漫画家,条形码计划也已告成,奥斯陆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变化?一切都留给观众自己观察。 我的家乡在我成长起来的这些年城市景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我留有记忆的场所都已经消失。有时候会有点遗憾,要是能在它们消失之前也记录下来一部分就好了。中国这么些年飞快的城市化进程下,其实很适合拍这样的系列电影,记录城市里的人的故事。
最后,提尔导演貌似很喜欢的这个广场在这部里没出现,我还有点小失落。不过也许有其他的什么场景贯穿了这三部电影,只是我没发现吧。
 《重奏》中两人共同喜爱的作者史达尔家附近
《重奏》中两人共同喜爱的作者史达尔家附近 《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中的回音场
《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中的回音场提尔导演确实很擅长拍人的意识和记忆与时空微妙的互动,三部里都能感受到这种奇妙的跳跃。很感谢他用镜头让我喜欢上一座城市,希望未来我有机会去奥斯陆把这些地方都走一遍。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如果你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是会如释重负还是如坐针毡?
近来有一部讲述《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电影,戳中了许多影迷的软肋。这部获得戛纳、奥斯卡多项提名的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却又触及四方的女性成长图景:女主朱莉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不断自我觉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女性。但在30岁的年纪,她仍然身处一种庞大的迷茫之中。
影片的序曲,学生时代的女主会把手机锁起来,这个时代太多的信息涌入,有时候她不得不把这些声音切断。短短几分钟,让我们看到了她经过自己的选择、尝试,学习医学、成为摄影师等跨度极大的学业和职业路径。遇见不同的伴侣,但都未等来结果。
影片结束你理解了她对自己的定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30岁的朱莉,在她的生活里遭逢了种种“可能”,遇到了爱、遇到了性、甚至遇到了相知和了解,最终仍旧孑然一身地生活。当然这个时代的女性早已知道,孤独并非是一种损毁。但它所对焦的那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共通的困境。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平庸的大多数,如何去一砖一瓦地搭建自己的个体生活?如同影片所提示的,我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但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资格这样告诉我。
撰文|走走小姐
01
自由的尺度
看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那个下午,我觉得度过了一段绵长温柔的午后。
娓娓道来的生活际遇,仿佛是一场没有路标的奔跑。看似四处皆为道路,但却不知目的。同时,也堵死了许多失败后的虚妄借口。不能让长大成人后的我们说,假如我当时……就好了。别说没有假如,就算像女主一样试过了种种“假如”,也仍难得到一个确切的圆满。女主拥有做选择的机会、去实践的成本,遇见了一个恋人后还有恋人。她把我们曾想过的尝试都活了一遍,但这不是一个鸡汤励志故事,她最终并未功成名就地成为一个“人物”。
影片结束,我像是在看另一个维度的自我裸奔。觉得喉咙发紧,张了张口既说不出话也流不出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不就是在说我们每一个充满期待却又无力回天的人生吗?
英国作家朱莉娅·塞缪尔在《生活即变化》中写到:尽管我们想速战速决,但情感与外部事件的同步需要时间,我们无法强迫自己的感情跟搬家货车,或是新工作、新角色、新身份一样齐头并进。从小到大,我们以为生活是向上的旅程,是通往更美好境地的阶梯,每一阶都更上一层。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更不确定,它有起有落,唯一确定的就是变化。
而我们似乎唯一能做到的即是:接受在这个世界动态地生活。这也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它没有完美的大结局,就是在讲述真实的成长,探讨了女性的恐惧、焦虑、悲剧、爱欲和生活本质的流动。
朱莉和前任分手时说“我觉得我就像是自己人生的观众,就像是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出演配角一样。”活不到自己的期待,是大多数人的现实。面对自我是一门艰深的功课,之所以选择“30岁”也大抵是这个原因。处在这样一个退无可退的成年世界门槛,突然赤身裸体地面临周遭无数无法命名的审视。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难道人生至此,就一定要交上婚姻、社会价值反馈的答卷了吗?我不知道,但也似乎正在经历这场无名的考试。现代人的生活,太容易被一种奇异的统一步调所控制。我们的感动和体悟,由四面八方的社交平台集体呈现。追求趋之若鹜的共鸣,缺少“少数和个性”的生长空间。交不上社会答卷的,头上仍有“隐形后进生”的帽子。
但更困难的是,朱莉真正痛苦的深渊在于:内心挣扎尖叫的“自我”并未出生。
每一段尝试后的生活似乎都不是她要的生活,每一个交往着的恋人都无法让她开启另一段人生。她狂妄的、渴求着被看见的“自我”如此虚弱、不堪一击、模糊和破碎。
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的否定。在自由尺度中的探索和游走,也如涉险于一片白雾笼罩的山林。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但自我的匮乏不是朱莉一个人的困境,它是这个时代呈现给我们的难题。在“资本冲动”的笼罩下,无论是社交媒体的热点追踪还是消费内容的同质化倡导,人们关注的内容(精神性的)和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很难为这个世界再贡献个性。
所以当我们从“塑料生活”里想找些本质,询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份特别的、让我们可以抛弃一切、超越一切的情感,我们也很难有决绝的选择。
是生活强烈的随机性,让整个时代的人类开始漂流。女主角身上心里无名的不安,生活选择上的不断尝试,潜在着结束这种漂流的欲望,和茫然无措的失落。犹如身处宽阔海面,想在此留下一点痕迹,却发现不过雨滴一颗。但她想做一块儿磐石,人类的“自我”就是超出生物性和自然性的存在,是文化性和精神性的产物,成为“磐石”的愿望,就是建设生活意义的起步。
02
进行中的奔跑
这部电影的导演约希姆·提尔是挪威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的表亲,他在北欧迷人富足的挪威首都奥斯陆长大。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地也来自这里,终年温润的温带阔叶林气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是全欧洲最富有、安全、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城市之一。但就是这里,一个代表着诸多文明尺度的地方——仍然令我们窥见了女性在起跑阶段的共通困境。
她有着所有缺陷人格角色在城市生活的核心危机:缺乏父爱的单亲家庭,无处着力的事业,对于性和亲密关系的不安,以及因此被贴上的标签。
女主虽然在尝试书写大胆新潮的女性宣言,但没有一刻是真正自信的。她对父亲的愤怒长久沉寂。她写完的文章羞于发表,被恋人赞美时仍然难于安然承认。她内心的彷惶不安,她对浪漫关系的追求,也在为她制造新的痛苦。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讲述恋爱关系的细腻是非常可贵的。所以电影非常好看,那些浪漫迷人的处理让整部作品无论讲述多么下沉的话题,都仍然是灿烂的。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比如海报上女主奔跑着的笑颜,就是在去见新恋人的路上。有一段美丽的超现实镜头:那是一个清晨,和同居男友如常的一天开始了。她打开一盏灯,一切都静止了。四处的山川、河流、草坪和人群全都存在,从日出到日落。但跑过这几个街区,她要去见心头记挂的新鲜爱侣。两人交谈、缠绵、拥吻,那一切美好的事物虽然存在,但都比不过她此刻正在进行着的“美好”——fall in love。
而回到现实中的现实,和同居男友爱情的灯盏熄灭了。她选择分开,她要继续新的关系,虽然最后仍旧在重复和增添着新的痛苦。两段展开描述的恋情最核心的关系矛盾在于“生育”。一个平权意识“应该较为成熟的地方”,“生育”依然影响着在这里生活的女性,该如何选择和她的伴侣继续后面的人生。
她也曾尝试过跟随男友去参加家庭聚会,和那些以“家庭”为单位的朋友们度过了孩子奔跑、大人尖叫的周末。在那浓缩的家庭体验中,无数婚姻世界的裂缝扑面而来。女主也和当时的男友不断地争论,男友会说着“很多人自己还没活明白就有孩子了”,一边仍不放弃说服她“我已经四十岁了,你比我小许多,我不能再等了。”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尽管男主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漫画家,会和女友进行深入的交谈,似乎欣赏她的表达赞美她的文章。他依然以一种“软压力”的方式在说服自己的伴侣帮助自己完成为人父母的心愿,即使这不是对方此刻的心愿。
当然,女主不是受害者或者值得同情的弱小女孩,她是一个受过教育、拥有选择能力的都市女性。但同时她依然对自己的困境毫无办法。以至于当意外怀孕来临,她也面临着时刻动荡不安的心。这部电影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在以女性作为感受中心去讨论女性遇见的问题。最后,当孩子又意外离开时,她悲喜交集的表情里也有松了一口气的安然。
梁永安教授在解读《小妇人》时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生命的打开,内部世界的多元化,一个人有更多的价值和更广阔的选择性。经历了城市化、中产化,经历了丰富的社会变迁,个体积累了大量的差异性。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女性对这个世界更有一种蓬勃的要求,反叛精神更为强烈。”女性在各种社会文明化之中,在发展、失序和建立新的脉络的过程里,开始迸发更丰富的诉求。片中的朱莉处在女性成熟度最好的30岁年纪,但为什么身处如此良好的社会环境,接受如此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仍在这个年纪处于呈现出自毁式的迷茫呢?而朱莉的状态甚至是世界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她在生育和婚姻问题上的被动、她对身份建设的自卑、她在面对自我社会价值上的迷乱。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去年有一部90后女导演的电影《爱情神话》,就以非常轻巧的方式在探讨女性的欲望和诉求。一个幽默的桥段是,前妻一脸认真地说出“我只不过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在调侃和嬉笑里,释放了性别平权的巨大信号。
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部电影中的三位女性都全权以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作为中心,颠覆了老白(片中男主)的种种预期。是近年来中国作品中,呈现女性自主性、自由度最宽适的作品。这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女性行为上存在一种共性:从男性的眼光、逻辑、要求和期待中,跑了出来。
 《致命女人》剧照。
《致命女人》剧照。但跑出来之后呢?
离开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的那些规则体系之后,我们新的人、新的女性,在前往新的环境下继续往前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有新的命题出现,也是朱莉正在面临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需要什么样的生命追求,去构建比较幸福的“个体生活”。
但跑,是前提。不论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还是《爱情神话》,或者《致命女人》到国内不断出现的《爱很美味》《我们的婚姻》等,都无一不在呈现着越来越强烈的女性主体性,先让“自我”离开此前的束缚,是全球女性进行中的动作。
03
第一人称单数
“三八妇女节”时,日本女性主义先驱森崎和江女士说过的话又被大家纷纷转发:我们要退回扣在女性头上的种种称呼,回到无名。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名字,母亲、妻子、主妇、妇人、姑娘、处女……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第一人称单数”,也是这部电影接近尾声的章节标题。
前任患了癌症离开,朱莉也又结束了一段恋情,她一如我们初见她时一样,好像又回到了一个人的自由迷雾之中。但终究还是不一样了,走到过“一切的尽头”,陪伴过昔日的恋人永别。她坐在海边,看着朝阳一点点升起来,阳光洒在她的脸庞,生活如此,都会心碎。她携带着这些过往,继续着三十岁以后的人生。
作家史铁生曾经写过一段对人生精妙的总结:人间这出戏剧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一代代角色隐退,又一代代角色登台,仍然七情六欲,仍然悲欢离合,仍然是探索而至神秘、欲知而终于知不知。
所以坐在海边听闻噩耗的朱莉,虽然流泪但并无更多感伤。因为你知道她会坐起来,还有后面的故事发生。我说电影很温润,是因为如朱莉般的女孩可能都经历过几段感情、人生里开始过不同的序章,有过不确定的放弃和继续着不确定的以后。在探索、寻觅、兜兜转转的过程里,开始接近那个藏匿的“自己”。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到了这里,电影超脱了关于性别的束缚。它开始讨论的是任何对成长有渴求的人:我们面临的不过是为这个“自我”重建坐标系。
它像陪伴着女主和无数潜藏在这样人生档口的年轻人一起,剥去一层恐惧和焦灼的外衣,让温柔和耐力展露出来。好像不必在面对海量涌入的信息而不知所措,大多数的社会比量开始失效。
女性的成长往往是从向内寻找开始的,她不再去渴求新一段的关系,新一份的职业,而开始选择在自己的遭遇中不断前行。所以在片中后记,看到她举起相机从容地引导着生涩的女演员。她能够为其他的女性提供信任的力量了,这时候电影所触达的连接如此敏锐,不只是在奥斯陆而是和世界上各处的女性一起犹疑、绝望、在平庸和想象中反复横跳。
我常用平庸生活将自己包裹,但每时每刻,作为自己人生的观众,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只能是我,对自己下这样的定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我拒绝成为被审判者。这个片名,妙就妙在它既是一种反馈也是一种自言。但除了“第一人称”的我,谁也没有资格告诉我。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走走小姐;编辑:走走;校对:赵琳。题图来自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